
- 编外人(鏟禄沈郁)最新完本小说推荐_免费小说推荐编外人鏟禄沈郁
- 分类: 其它小说
- 作者:鏟禄
- 更新:2025-07-06 21:57:54
《编外人(鏟禄沈郁)最新完本小说推荐_免费小说推荐编外人鏟禄沈郁》精彩片段
下雨了,七月的雨来得没声没息,像是有人在屋顶上抖开了一层湿漉漉的旧报纸。
沈郁抬头望了望天,雨落得斜,风有点冷。他没带伞,
手里只拎着那只用了三年的深蓝文件包,皮角磨得起了毛。等他走进市政大厅前厅时,
裤脚已经湿了一半,鞋里也渗了水。他原本不该在这儿。半个月前,
组织口头通知他“临时借调至市纪委办公厅综合协调组”,时间两个月。
理由简单:人手紧张,急需经验干部支援督查任务。没有人征求他的意见,
也没人解释为什么是他。更没人告诉他,这次借调,
最终会变成他这十年仕途中最难消化的一次“调令”。“沈主任?” 前台的小姑娘喊他。
他顿了一下才反应过来,现在他不是“沈主任”,是“沈同志”,借调干部,无编制权限,
无指挥权限,无直管职权。他笑了笑点头,把胸卡别在胸口左侧,
一排黑字写着:“综合协调组 · 沈郁”。“这边请,王副组长在六楼会议室等您。
” 她说完,用一种试探性的目光看了他一眼——那眼神里有点困惑,也有点……怜悯。
电梯上行的间隙,他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四十出头,脸色白,眉心有道疲倦的竖纹。
他忽然想起三年前调任区府办时,他妻子说过一句话:“你要是能熬过这一层,
就能喘口气了。” 他当时点了点头,现在回想起来,只觉得讽刺。六楼,
会议室的门半掩着。沈郁敲了敲门,推门进去时,一股烟味扑面而来。“来了?坐吧。
” 王副组长头也没抬,正低头翻一份卷宗。他穿着一件洗得有些泛白的衬衣,袖口卷起,
一看就是常年在基层“磨”的人。他身边坐着一个年轻人,二十七八岁,皮肤白净,
神情冷静,见沈郁进来,只点了点头。“这是我们协调组组员,小杜。” 王副组长说完,
才抬头看了沈郁一眼,那眼神不带欢迎,只带一句话:“你是临时的。”“我们这个组,
负责市属重点项目招投标过程中的流程监督、资料对接和信访舆情预警。
” 王副组长翻出一份材料,扔到他面前,“这是昨天的数据汇总,你先看看,
熟悉一下流程。今天下午三点,我们要去市城乡建设局,
例行抽查他们‘XX新区’的三个招标项目材料。” 他话音刚落,
又补了一句:“市领导盯得紧,出了事小组要背锅。”沈郁默默翻着材料,一页页扫过去,
纸张冰凉,信息密密麻麻。 他心里清楚,这种借调任务,表面是协调,
实则是“踩点”:踩谁的点,什么时候踩,踩了之后有没有“脚印”,全看谁给的“鞋”。
两点五十,市纪委办公楼门前,一辆灰色公务小车静静地停着。沈郁坐在副驾驶,
小杜坐在后排,王副组长一手夹着烟,一手握方向盘。“这项目以前查过?”沈郁问。
“查过,但那是去年。”王副组长眼皮都没抬,“今年换了分管领导,施工单位也换了,
人还是那几拨人。就是手法更细了。”小杜突然插了一句:“你看过去年的招标文件了吗?
”沈郁回头,“还没。”“建议你看看,特别是招标单位授权代表的签章部分,
有一家去年用的是假公章,纪委立案了,但最后不了了之。”“为什么不了了之?
”小杜没回答,只是盯着窗外。 雨还在下,密密麻麻的滴打在挡风玻璃上,
像是某种暗语——说不清,也听不懂。三点整,车停在市城乡建设局门口。王副组长熄了火,
沉声道:“沈同志,这不是你熟悉的地方,也不是你能决定的事。你今天就做一件事——看,
不动,记下来。”沈郁点点头,推门下车。他不知道,今天这个普通的借调检查,
会引发一场牵动多个系统的反向回涌。而他,也将在这场博弈中,被迫撕开他的身份外壳,
看到自己最不想面对的那一面。他以为自己是来借调的。实际上,是被“借”来试毒的。
市城乡建设局的接待室窗明几净,空调开得略冷,墙上挂着一幅宏伟蓝图,
标题是《XX新区基础设施一体化工程布局草案》。沈郁站在图前看了几秒,
不动声色地走向座位。会议桌边,已经坐了三个人,均为建设局方代表,
最右边那位戴着眼镜、年近五十、衣着笔挺,一看就是“场面人”。他起身握手,
笑容得体:“纪委的同志辛苦了,今天这雨说来就来,路上还顺吧?”“顺。
”王副组长简短作答。 他将文件包搁在桌上,环顾一圈,“今天抽查项目,
三份:道路招标一、建筑工程二、电力铺设三。材料带齐了吗?”“都在这了。
” 中年人拍了拍放在桌上的三套文件袋,贴着红色编号:“这是道路项目的,
这是建筑项目的,这是电力的。”沈郁坐下,接过第一份标书。他翻得慢,指尖划过封面,
“项目编号:Z-0325,道路养护、排水系统整修与绿化工程……开标时间三个月前,
承建方是‘广通建设集团’,中标价四千九百三十七万。”“广通啊。”王副组长语气平淡,
朝小杜使了个眼色。小杜会意,从包里掏出一个A4文件夹,
“这是我们协调组目前掌握的历史中标记录,广通今年以来共参与投标12次,
成功中标9次,命中率……75%。”房间一下子沉了。中年人笑容有些挂不住,
辩解道:“广通资质是全市前三,报价也算合理。招投标流程全程都有录像存档,
我们欢迎纪委随时查验。”“录像我们会调。”王副组长说完,又翻了一页,
“你们招标小组今年有没有换人?”“主要负责人换了一位,是从原交通局抽调过来的。
” 那人顿了顿,补充道:“这位姓鲁,经验丰富,素质可靠。”“鲁?”沈郁翻到尾页,
看见盖章单位写着“鲁建文”。他记得这个名字。五年前在区府办时,
鲁建文曾因项目资金流向不明被组织调查过一轮,虽然最终“未构成实质违规”,
但从此沉寂,调离岗位。如今又回到招标口,
且主导中标率如此之高的公司评定……“鲁主任今天在吗?”他问。“在,在的。”对方说,
“不过今天他去市政院开专家论证会,回来可能要晚一点。”“没关系,我们材料先带走。
”王副组长抬了抬下巴,“视频拷贝一份,原件复印两份,卷宗目录请现场列明。
”沈郁补充:“还有评标专家名单和签到表。”中年人点头,脸上堆着笑,“我马上安排。
”出了会议室,小杜轻声道:“广通这个公司去年没这么高命中率,一直到今年三月,
换了评标主持人之后,中标率陡增。”“你查查鲁建文最近半年有没有大额资产交易,
或亲属企业往来。”王副组长吩咐,“查不到也无所谓,先把数据摊开。”“沈同志。
”他转头看向沈郁,“你刚进组,有些事情我们不便说太满,但纪委查的不是数字,是人。
中标价只是一串数字,后面的评审打分,才是灰处。”沈郁点点头。他从业多年,
自知此类灰处极难揪实:评审打分属主观性项目,只要不太离谱,
再高的命中率也能从“合理性”里溜走。但真正让他在意的,是鲁建文。
这个人被系统“沉底”过一次,却又在某种默契中“浮上来”,而这回水面之下的漩涡,
怕是比上次更深。回程车上,王副组长打了个电话,压低声音:“……目前材料初步摸清了,
项目方配合度高得反常,鲁那边联系不到,估计是提前听了风。
你那边让纪委信访口准备预警通报,轻点放,不要惊动上头……”沈郁靠在车窗边,
望着窗外的水珠一滴滴往下滑。他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这次借调,可能不是临时支援,
而是某种“人事排雷”。他被丢进一场连草图都没画完的局里,
被迫以一个“外来者”的身份,去做“决策者”用不上手、但“执行者”也不愿碰的事。
而这个局,很可能已经不是纪委层面能控住的了。晚上八点,市纪委办公楼灯光未灭。
他刚端起一碗泡面,小杜推门进来,脸色严肃:“查到了,鲁建文的外甥女,
去年注册了一家咨询公司,叫‘昱承项目策划’,
主做‘项目流程优化’……刚刚广通的投标文件里,技术标一栏就写着:‘策划方:昱承’。
”沈郁放下筷子。 这,不是普通借调能收场的活了。沈郁手指敲了敲泡面碗沿,
腾起的热气在眼镜片上氤氲出一层薄雾。他抬头盯着小杜手中的纸页,
那份“昱承项目策划”的工商注册资料简洁得不像话:一页,白底黑字,没有任何异常。
正因为太干净,才显得可疑。“注册地在郊区的一间商务楼,法人叫周忆菲,23岁,
毕业于省内三本院校,工商资料留的是广通集团的对口邮箱。”小杜语速不快,“刚查的。
”“她和鲁建文之间,有户口或直系关系吗?”沈郁问。“户籍地不在一处,
但她母亲的户主名和鲁建文妻子相同。应该是外甥女。”沈郁没说话,
只从抽屉里拿出一本便签本,
在第一页写下几个字:“昱承 = 关系户 + 评标策划”这是潜规则吗?是。能查吗?
也能。但能不能立案,那是另一回事。“你怎么看?”他抬头问小杜。“正常流程下,
不构成立案。”小杜表情冷淡,“策划公司作为技术标辅导方,并非直接投标人,
也不属于公务员体系,且目前未发现资金往来与评审干预直接证据。”“但他们绑定了。
”沈郁说,“绑定本身,就是变相的筹码。”小杜点点头,“可惜的是——法条管不到筹码,
除非它变成了现金。”沈郁明白这句话的分量。纪委不是法庭,不靠定罪吃饭。
他们管的是风气,是纪律,是组织原则。但当风气变成“大家都这样”,
原则就成了一纸空谈。“你觉得这活,是纪委真想查,还是有人想让我们‘看见’?
”沈郁语气低沉。小杜没回答。他知道,年轻人越沉默,说明他越清楚其中隐线。而他,
作为这场借调调查的“临时成员”,却越来越像一块被放在棋盘正中的垫脚石。第二天上午,
市纪委信访室发布了一份“项目评标异常数据月报”,挂在系统内网首页第七行,
阅读权限为“处级以上”。
通报文字写得极其克制:“建议相关单位对部分评标策划行为开展自查,完善内控流程,
防止因‘非本单位人员介入技术评分过程’造成系统性风险……”沈郁点开那份通报时,
办公室里只有他和王副组长两人。“这是试水。”王副组长点燃一支烟,声音模糊,“放风,
看谁先跳。”“你是说,通报不是发给外面的,是发给……系统里人的。”“对。
”他吸了口烟,“纪委查案,有两种手法。一种叫‘拉网’,一张大网撒出去,
看漏网之鱼跑哪儿;另一种叫‘诱鱼’,放点饵,看哪条鱼先动。”“那这次是哪一种?
”“我不知道。”王副组长盯着窗外,“我只是个副组长,我只知道,
市领导对‘XX新区’项目背后的资源配置,不止看数字。”资源配置。是啊。
一个新区的每一寸土地,每一个标段背后站的,往往不是企业,而是人。是系统内的“人”。
而纪委,是“查人”的,不是“查企业”的。下午三点,
小杜从市建设局拷回了招标录像文件。沈郁一帧帧看过去,眼睛看得发涩。
就在第二份标书的开标会上,一处细节引起了他的注意——评标专家签到表中,
第三位专家签名略有涂改。“这个签名?”他放大画面。小杜走过来看,
“这个专家叫黎东林,本是省建院外聘专家,但据我们系统专家库记录,
他今年并未出现在‘可抽取名单’中。”“什么意思?”“就是说,要么是误抽,
要么是人为替换。”“黎东林有案底吗?”“查了,干净。
但他女婿在广通下面的施工子公司任职。”沈郁低头,
续在便签本上记下一笔: 评审替换+专家关联+投标策划=精准命中这是一起系统性操作,
不是偶然。他终于意识到,广通这个公司,从表面资质到内部策划,从评审人选到中标过程,
全是“设计过”的。“我们,是不是踩到别人布的网了?”他问。王副组长沉默片刻,
说:“网不是现在布的,是两年前就布下的。我们现在才看见,是因为有人想让我们看见。
”“那你呢?”沈郁盯着他,“你想不想看见?”王副组长笑了笑,
烟头在烟灰缸里闪着红光,“我不是你,我从不想看清楚。因为在这儿,看得越清楚,
死得越快。”沈郁回家的时候,已近深夜。客厅里没开灯,妻子睡得早,孩子寄宿学校。
他靠着厨房门发了会呆,忽然觉得屋子里有点冷。他想起十年前初进体制时,
最常被领导灌的一句话:“清白,不是你不拿,而是你知道拿了之后会死。”可现在,
越来越多的人拿了,却活得挺好。这比腐败更可怕。这叫“共识”。
他握了握手里那本便签本,几页纸,轻飘飘,但写着的,可能是一个新区背后的风向转折点。
而他,不小心站到了风口中央。周五早晨,市纪委办公楼的走廊略显空旷,沈郁到得早,
特意提前半小时到了资料室。他要查一份三年前的“新区筹备会议纪要”。
这份纪要当年由市发改委牵头、城建局执行,是“XX新区”正式立项前的关键材料。
那一次会议,定下了新区的规划格局、资金路径、初始施工单位及项目审批流程,
换句话说:定了整个棋盘的排布。可奇怪的是,他翻遍了项目档案盒,
却发现该文件只存“议程简表”,而会议纪要本体不在。“这个资料原本在吗?
”他问资料管理员。管理员年纪偏大,戴着一副老花镜,翻了翻笔记本说:“按规定是有的,
但去年年底有批档案转去市府督查室审阅,可能还没还回来。”“你能看到调出记录吗?
”“看不到,调档记录是封闭权限。”沈郁皱了皱眉。此时,
他终于确认:有人在控制资料流通。而被调走的那一份会议纪要,不是随意的一页纸,
它有可能记录了某些在正式项目开始前、就已被“定向”安排的资源分配。他心里一沉。
如果这事向下深查,碰到的不仅仅是“评标腐败”,
还可能涉及当年参与拍板立项的**“决策链”**。回到办公室,小杜已经等着他,
手里拿着一份刚打印出来的文件:“广通集团2019年至今的招标数据统计。
”他递给沈郁,神色复杂:“我算了一下,广通在新区三大板块累计中标23个项目,
占新区项目总数的42.6%。”“这比例过高了。”沈郁喃喃。“不止。”小杜补充,
“我们通过公开资料比对发现,有7个项目的评标负责人,是同一套三人组合。”“三人?
固定评标组?”沈郁一惊。“没错,虽然评标专家库是系统随机抽取,但这三人,
名字反复出现在多个项目里——而且他们都有共同点:都是市建设系统退休返聘人员。
”这就是内部合谋+制度空窗最典型的表现。评标机制“形式上”随机,但在操作层面,
早就被某些“活系统”攻破。他深吸了一口气,缓缓开口:“我们必须写报告了。
”小杜抬头看他,语气忽然一变:“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这件事,如果真的捅上去,
牵连的不止是建局和广通。上面立项签过字的人,可能都要被问话。”沈郁看着他,
声音低却坚定:“我知道。”“可你不是纪委的人。你是借调的。”小杜的眼神冷了几分,
“你有没有想过——借调干部动了系统布局,最后,谁来保你?”话说出口,
办公室陷入短暂沉默。沈郁没回话,只走到窗边,看着外面灰白的天空。
他忽然想到一个词——“限界点”。系统里的每一个人,都在试探那个边界;而他,很可能,
已经站在那条线的正中央。报告交上去的当天,王副组长请了假,说是回老家“办点私事”。
沈郁一人代表协调组,把那份写得克制又精准的调查建议书,
提交给了市纪委第五室分管副主任。副主任姓唐,五十岁出头,着装严谨,眼神淡漠,
看完报告第一遍,没有任何表情。他合上文件,语气平静:“材料写得不错,
节奏把控也有分寸。”“但?”沈郁问。“但这个节点,未必适合深查。
” 唐主任放下文件,直视他,“新区是今年全市工作的重头戏,牵扯太多。
一旦你这个建议被采纳,就要启动立案调查。你清楚,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要改一条早就建好的水路。”沈郁淡淡道。“对。”唐主任靠在椅背上,
换了个角度审视他:“你是不是还不太明白,纪委不是什么都能查的。我们是‘纪’,
不是‘律’。”沈郁点点头,语气依然平静:“我明白。可我们查的不是人头,是方向。
”“谁告诉你,我们查的是方向?”唐主任忽然冷笑,“纪委查的,
是共识里允许查的部分——那些已经没人护着的,才叫问题;而那些还有人护着的,叫资源。
”话音落地,空气像是被压了一层霜。沈郁沉默几秒,说:“那我能不能知道,我这次借调,
到底是因为需要,还是因为——我要被‘识别’?”唐主任顿了一下,意味深长地看着他。
“你能问出这个问题,说明你已经被识别了。”下班后,沈郁去了妻子所在医院接她。
妻子是内分泌科副主任,工作极忙,一年都难得坐一次班车。
今天她特意发了信息:“我想你接我。”两人坐在车里,窗外霓虹拉出淡蓝色的影子。
“你最近很累。”她说,“我看得出来。”沈郁笑了笑,“有点。但也还好。
”“你以前做决定都很果断,这次怎么……有些犹豫?”“因为以前我做的决定,
顶多影响自己;但这次,我可能会影响一个系统。”“你怕吗?”沈郁沉默了一会儿,
说:“我不怕他们,我怕我自己不知道自己到底想成为什么人。”妻子没有回答,
只轻轻把手搭在他手背上。那一刻,他忽然觉得:也许这一切都不是查案,而是认人。
不是组织认他。是他在认自己。沈郁没想到,唐主任签批的反馈比他预期还快。
周一早晨八点半,纪委协调组微信群里弹出一条新通知: “沈郁同志于本周起,
驻点市城乡建设局,开展为期两周的联合督办调研。”他盯着“驻点”两个字看了好久。
不叫“借调”,不叫“专项核查”,叫“驻点”。
这是一种官场术语里模棱两可的表态方式——既不等于立案调查,也不是日常视察。
它是介于信任与怀疑之间的一种“半信任”,是一种“暂时允许你存在”的姿态。
更关键的是,驻点人员不会配备专属组员,也不代表纪委正式发声。这意味着,
沈郁将一个人,带着协调组的临时身份,
进驻到一个他怀疑正在运作系统性掩护机制的单位中去。这不是查案,这是“放人入局”。
市城乡建设局的综合办把一间靠走廊尽头的临时办公室收拾出来。 窗小,墙皮发黄,
办公桌抽屉里甚至还有上一任临时工作人员留下的便签和一盒已经变味的茶叶。
沈郁把自己的文件包摆上桌,只带了一本笔记本和一台加密U盘的笔记本电脑。
他不需要其他。他知道,在驻点工作里,“轻”是生存法则。综合办的王科长来打了招呼,
一脸热情:“沈哥,这段时间你就是我们单位的老前辈了,有事尽管说话。
”沈郁微笑:“不用太客气,调研而已。”“听说你原来在府办带过项目线?”“嗯,
跑过几年。”沈郁随口回道。“那太好了,我们局这些年最怕协调上的事卡脖子,
有你指导一下,我们也能理顺点。”话音落地,两人彼此一笑——都知道对方在演,
但都照剧本演。第一天没人给他安排具体任务。第二天上午十点,
市建设局副局长廖文炜亲自到他办公室喝茶。廖文炜是副局里头面人物,一身黑色短袖,
发型油亮,气质儒雅,进门便笑:“早就听说纪委来人,还是沈主任,真是稀客。
同类推荐
 妻子的精油瓶精油林薇最新好看小说_已完结小说妻子的精油瓶精油林薇
妻子的精油瓶精油林薇最新好看小说_已完结小说妻子的精油瓶精油林薇
工科生爱玄幻
 东汉道士在民国当差(周婉清冰冷)完结版免费阅读_东汉道士在民国当差全文免费阅读
东汉道士在民国当差(周婉清冰冷)完结版免费阅读_东汉道士在民国当差全文免费阅读
巴拉巴拉六毛八
 别碰我顾琛林薇薇全章节免费在线阅读_《别碰我》精彩小说
别碰我顾琛林薇薇全章节免费在线阅读_《别碰我》精彩小说
一座海岛
 命绝红色嫁衣万钧小茹热门小说阅读_好看的小说推荐完结命绝红色嫁衣万钧小茹
命绝红色嫁衣万钧小茹热门小说阅读_好看的小说推荐完结命绝红色嫁衣万钧小茹
留其白
 氧气与法律条纹冰冷一种免费小说完结_最新章节列表氧气与法律条纹(冰冷一种)
氧气与法律条纹冰冷一种免费小说完结_最新章节列表氧气与法律条纹(冰冷一种)
不品细糠
 古镜寻君已成殇(苏清雅萧景珩)小说推荐完本_全本免费小说古镜寻君已成殇苏清雅萧景珩
古镜寻君已成殇(苏清雅萧景珩)小说推荐完本_全本免费小说古镜寻君已成殇苏清雅萧景珩
一见卿卿误终生
 雪崩群鸟高飞(艾岗巴于辉)热门小说_完结版小说全文免费阅读雪崩群鸟高飞(艾岗巴于辉)
雪崩群鸟高飞(艾岗巴于辉)热门小说_完结版小说全文免费阅读雪崩群鸟高飞(艾岗巴于辉)
周筱珺
 石缝里的蔷薇林晚沈泽宸热门的网络小说_完整版小说石缝里的蔷薇(林晚沈泽宸)
石缝里的蔷薇林晚沈泽宸热门的网络小说_完整版小说石缝里的蔷薇(林晚沈泽宸)
呦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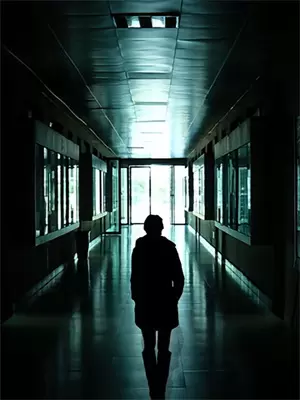 陆远和陈默(陈默陆远)全章节在线阅读_陈默陆远全章节在线阅读
陆远和陈默(陈默陆远)全章节在线阅读_陈默陆远全章节在线阅读
甜甜糯糯的栗子
 老槐树张老蔫(我请邪神杀村霸)全本阅读_老槐树张老蔫最新热门小说
老槐树张老蔫(我请邪神杀村霸)全本阅读_老槐树张老蔫最新热门小说
时光浅不浅







